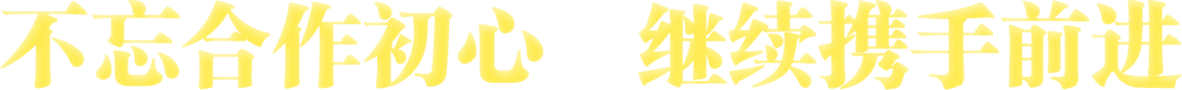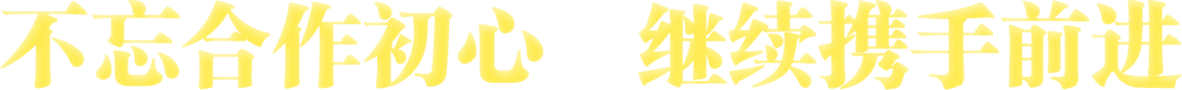小雪过后,气温骤降,在黎平县双江镇黄岗村,吴和全一家正在盖新房,和寒冷的天气截然不同,此时他心里有着无限暖意。这一刻,他等了二十多年。
在侗寨,孩子出生,父母会在山上种一片树木。树木成材作栋梁,孩子成人要独立,便请木工给年轻人盖房子。从今年四月伐木建房,如今新房已进入盖瓦阶段,看着地面运送瓦片的竹筐离房顶近一点,吴和全内心就多充盈一分。
虽然只是建造几间简单的木房,但这里面包含了父母对孩子的美好祝愿,是一个人成家立业的标志,也是侗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秘诀”。侗族文化不仅“藏”在音乐、服饰里,还蕴含在一块块木头搭建的建筑里。
“生死都离不开鼓楼”
行走在黎平乡间,只要看见鼓楼,就知道离侗族村寨不远了。
无论是出于对鼓楼建筑的好奇,还是被鼓楼里生起的烟火吸引,你会无端生出一种走进它一探究竟的念头。
作为与侗族大歌、花桥齐名的“侗族三宝”之一,鼓楼对侗家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什么叫鼓楼?因为鼓楼顶端真的有一面鼓。”坐在黄岗村鼓楼里的火堆旁,村文书吴显金指着鼓楼顶部说道。
鼓楼是侗寨的标志,也是寨中民众集会和议事的场所。侗族鼓楼本名“堂瓦”,意为大家活动的地方。清嘉庆年间的《广杂著》对此有“每寨必设鼓楼,有事则击鼓聚众”的描述。
“鼓楼跟历史上的烽火台差不多。只是平原地区用眼睛看(烽烟),我们山区用鼓声传递信息。鼓点不同,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同,过年会敲欢乐鼓,遇到火灾等紧急事件又是不同的节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研究员邓敏文说。
在侗寨,村寨往往以鼓楼为中心,因此,一村一寨会以房族或几个姓氏合建鼓楼。
“先修鼓楼,后起民房立寨”,这是千百年来侗族人家建寨遵循的古训。鼓楼就像侗族群众种下的一颗不断生长的“文化植物”,而环绕着鼓楼生活的侗族人家,也生生不息地传承着。
儿时在鼓楼嬉戏打闹,听大人唠家常;成年后在鼓楼行歌坐夜,成家立业;逝世后在鼓楼举行悼念,向众人宣告这个人“回去了”……鼓楼和村寨里的每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用吴显金的话来说,“侗族人生死都离不开鼓楼。”虽然鼓楼有传递信息、议事的功能,随着通信的发达已逐渐减弱,但鼓楼在侗族群众心中的位置却丝毫未减。
无论是鼓楼、风雨桥,还是房屋、禾仓等,这些不用一钉一铆建造的木质建筑,在黎平的崇山峻岭间星罗棋布,不仅形成了侗族特有的建筑结构,也搭建起了侗族群众的心之归处。
“掌墨师”终将老去
多年以后,坐在阳台上背靠着房板,望着自己修建的第一座房屋,年过古稀的黄岗村“掌墨师”吴光华尽管有些眼睛老花,但依然记得年轻时做木工的场景。
吴光华从小就痴迷木构建筑,到处偷师学艺,努力加上极高的天赋,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掌墨师”。经由他手修建的房屋、鼓楼、风雨桥遍布十里八乡。
“掌墨师”,字面意思为掌握墨线的师傅。在侗寨,“掌墨师”等同于侗族本土的建筑师。和常见的建筑从制图开始不同,“掌墨师”的“图纸”存在于脑海里,且自有一套算法和口诀。
在修建房屋时,“掌墨师”只需勘测建筑面积,根据雇主需求,就能快速在脑海里形成房屋的大体结构,估算出所需木材。并将各构件的尺寸、榫卯位置和大小等用墨线标示出来,木匠按线加工,房屋不用一钉一铆便能建造成功。
建造民居只是基本技能,鼓楼、风雨桥等大型建筑才见“掌墨师”的真功夫。在鼓楼建造过程中,掌墨师全凭一个墨斗盒、一把直尺、一根丈杆,便能将成百上千关系错综复杂的木梁、柱、椽、枋、板等材料标示清楚,衔接架构完成,就可达数百年不朽不斜。2006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以下简称“侗族木构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时代在发展,村寨在改变。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年轻人走出村寨,开过眼界的年轻人回到本地后,发现传统的木房子存在基本使用问题,比如保温、隔音等等,所以他们更喜欢砖墙结构。
在不少村寨,传统的木房子逐渐被砖混结构取代,这也意味着“掌墨师”的市场正在被逐渐压缩。此外,“掌墨师”大多是当地村民,这让他们难以获取资质进入市场,加上师徒制的学习方式,也让后续力量难以延续。
陆德怀是纪堂一带小有名气的“掌墨师”,师从侗族木构技艺省级传承人陆文礼。这些年,陆德怀没有沉浸在自己的名气中沾沾自喜,相反他时常感到年岁渐长的无力,因为眼睛不好导致不能在晚上画图,这让他很苦恼。
在黎平,现存鼓楼434座、戏台119座、花桥199座,有传统村落98个,居全国首位。支撑如此庞大建筑群的技艺背后,是一群积年累月的“掌墨师”,如今大多年过半百,终将老去。
“总有人正年轻”
尽管走南闯北很多年,参与过许多建筑设计,获得了不少奖项,但“無名营造社”设计师陈国栋朋友圈的封面,依旧是他刚到黄岗村设计的一个木构建筑——生态厕所。
陈国栋外号白毛,在日本京都就读博士期间的一个偶然机会,因黔东南传统村落的古建筑调研工作而逐渐醉心于这里的生活和建造。
用白毛的话来说,“从一个建筑师的视角来看,当时看到村寨里清一色的纯木结构建筑的景象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种干阑式木构建筑,在中国已经延续了7000年,而且到今天还一直活跃在日常生活中,这太珍贵了。”
2017年,他带着“無名营造社”的社员从日本京都回国,直接将事务所搬到了黎平茅贡。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不仅对传统木构建筑进行了物理性能的提升,也思考着传统木构建筑如何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诉求。
对于传统木构建筑如何走向下一个时代?在白毛看来,要回应“老百姓建造房屋、装修房屋不再选择木构建筑,‘掌墨师’高龄化、技艺如何传承”等问题,并聚焦产品研发,希望以半工业化的方式实现木构建筑的装配式。
如果说通过外部力量注入让木构技艺不断创新发展,那黎平集合多方力量培育发展,则不断增加了侗族木构技艺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今年7月开展木构建筑培训以来,目前已经有100多人获得了证书,这些证书能让从事木构建筑的手艺人更好地走入市场。”黎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培训的工作人员潘成美说。
为了更好地推动木构建筑的传承发展,黎平县依托省级职业技能培训基地落户优势,开展“理论教学+场地实训+工地实践”的木构工匠培训,不仅培养了木构技艺传承人,也解决了老手艺人的资质问题。
此外,为了确保该项技艺传承的便捷性、易操作性和完整性,黎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展了区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和建筑物的全面摸排、记录、建档工作,并进行数字化归档。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在黎平县,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在多方推动下,正朝着曙光一步一步走下去。
(来源:贵州民族报)